一篇旧文
2019-09-01
翻QQ空间,看到一篇2012年1月18日的文章,放在这里偶尔看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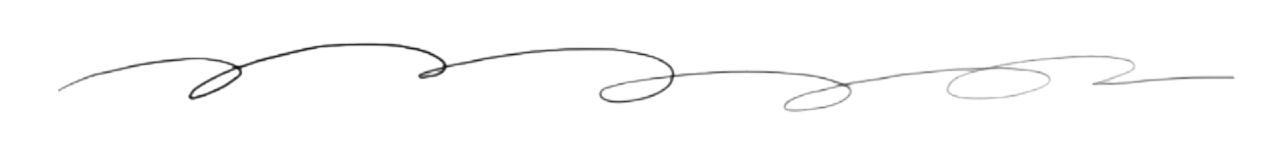
很久没有发现了,原来一年的疲惫与欣喜,可以像沙子一样顺着某种东西一涌而下,静流无声。楼上传来母亲叫我去吃宵夜的喊声,从楼道的另一边听来,空灵而回响。脑中有些类似于灰尘的东西随着声音微微震动,发生微小的移动,又像极了什么在心脏表面摩挲的感觉。手很冷,呵出来的热气隐遁在雾一般莽莽茫茫的黑暗中。音响中的旋律不合时宜地戛然而止,心跳随即停了半拍。
记得很小的时候,会纠结自己长大的志向。做总统。做科学家。做宇航员。做作家。做画家。做音乐家。等等。但我很小就知道怎么把自己折腾到一个走不出来的圈圈当中去:我似乎从来没有坚定过某一种职业并以之为我一生的理想,连梦想都没有过。那个很小时候的我,从来不会做同一个梦,从来不会像母亲一般,清楚地记得醒来几分钟前梦中的人与物,甚至对白,甚至神态。我因而常常活得不知所以,并且现在想来引以为幸。想这样小便活得清楚自在,纵是一个早熟的怪才也不枉可叹。那时候母亲手里已经有一本《周公解梦》,常常早上与我分享她的诡异的梦,且一直坚持早饭以后方肯告诉,无论我多少好奇。饭时,她会像讲别人那听来的故事一般娓娓道来,脸上的神色随故事的情节变化而变化。清楚地记得这样一次:“我夜梦梦见你外公带着我、你阿姨、舅舅和你外婆,逃拉村外头去。就是从你外婆家老屋出来,一直沿着那条本来经常走的小路跄出来,跄拉村口。”然后她略微地一顿,嘴角扬起来,说:“真奇怪,你外婆他们都搬出来这么久了,怎么会做这种梦!还有,我们是为了什么在逃呢?——你说奇不奇怪?”我当时不曾领会到母亲的奇怪,几年后的现在想来,我应该在年事见长的母亲脸上看到了小女孩的喜悦与新奇。那一幕,大概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忘记。
可是我终究这样活了如许的将近十年,对外界不闻不问,活在母亲厂里,活在家里,活在一个两个人的世界。
傍晚母亲回到家时,我正在看书,下午的暖阳捂得我一动不愿动。她匆匆放下包,快步走到阳台收被子。两床吐司一样暖烘烘的被子。我犹豫着说要帮她,她像是没听见,大半个身子爬出阳台,手支在被子上,一个一个地收夹子,从容不迫。我识趣地退开,脚磕到萨克斯的箱子。于是仿佛有某种力量怂恿着似的,我取出萨克斯一首一首地吹着,不会疲倦地吹着。我翻出四五年前因为简单而藏起不用的谱集,抖开厚厚的一层灰尘,一首一首地吹着,为我惊异地发现其陌生的曲子。就这样一个小时过去。最后,夕阳薄暮,血红的余晖里金色的管子啸叫着将一首know you by heart快半拍停下。我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仿佛少了什么,问经过身旁的母亲怎么样,她唯唯。回头,夕阳已经落到看不见的地方。
大概七八点的样子吧,母亲驱车携我到厂里。一年倒数第二天工日的晚上,厂里除了爷爷空无一人。爷爷是厂里的门卫。到厂里时,黑漆漆的厂房矗立在阴沉的乌云下面,只有门卫室里传出来乳黄色的灯光以证明人的迹象。老旧的电视机从那个不足五平米的房间发出些自言自语的声响。停下车,看见爷爷从车的后面踱过来,顿感安心。今天来厂里,是来送神的。我问了母亲很多次,是什么神,她或是不语或是冷冷的一句别问,从不停下手里繁杂的准备活计。我把四仙桌从三楼背下来,爷爷执意接过去搬到了要用来送神的车间。我看着他矮矮的黑色的背影迎着惨白的灯光走去,不觉心疼辛酸,不觉又一次不知所措。
拜神的时候,母亲仍旧那副严肃的模样,要我先拜,拜完了又叫再拜。于是再拜。恭谦地把香搁在不知所拟何物的香台上。然后又一个让我怎么也忘不掉的镜头出现:她轻轻地手持着一束香,一拜,下跪,站起,又一拜,再跪,然后再站起,再拜再跪,再站起,然后深深地一拜,上前半步将香插好。整个过程我气息屏窒,不敢直视母亲或是烛台,又不敢将头别转去,去看这苍白冷漠的厂房,看这幢幢的鬼影。我只是这样看着。插完香,母亲却不急着走开。她后退三步,然后,正立在那里,看着另一个人一般地正视这香台,这袅袅消散在雾一般黑夜的香烟。我不免下意识地也直立着,挺着胸站在那里,仿佛看着谁经过我的面前。闭上眼,干涩却不乏酸楚。
“好。好化纸了。”我睁眼,母亲已然悄无声息地走到身后的箱子边上。箱子里是要火化的纸元宝,一个个黄澄澄却轻飘飘,托在手中没有什么感觉。“别看了,快放好。”“嗯,我来吧。”我接过打火机,点着了其中一个的一角。火光乍起。
其实类似这样的事情,应该是从我很小就开始了——或许要远早于我“很小”的时候,但我那时并不知情。我所依稀记得的,是一年又一年,母亲在家里送完灶子菩萨,隔夜便领我到厂里送另外一个神仙——尽管我从未知道那神仙的名号,但我以为既然是神,便应是好的,是该受拜的。每每这种事情,最让人欣喜的莫过于化纸这一个环节,看肆无忌惮衍生的火苗吞噬着周遭的一切,看热与光无比接近自己的肌肤,看灰烬如熔融的黑玫瑰扬起又散落,看全然没有了希望的灰烬当中,忽的又生出几许闪动的火光。在无数个陪伴我独自前行的寒冬里,那是多少震撼我幼小心灵的仪式;而在那火光之中,又有多少不可语人的话。
送完神,爷爷说了这样一句话:“廿二、廿三说是要下雪呢。”心中一动,几日不见,却仿佛久违的感动与希冀。
放焰火的时候,躲在雨棚下面,天上锦花连连,我却像是在躲雨,多可笑。空气中弥漫着硝烟的气味,亲切而好闻。脚下窸窣是刚才如雨落下的石灰,明明很像冰雹的一颗颗东西,捏在手里却马上化作了白色的灰尘,扶风而去。
然后回到二楼的办公室,昏暗的冷色调的灯光下,看了一本王小波的《夜行记》,半本安妮的《素年锦时》,漫不经心地翻了翻奥斯丁的某书,甚至不很记得名字了。三个钟头后,感觉兴味索然。弃书离席。
窗外什么都看不见,听去却是雨声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