行李箱
2019-09-28
原本应该飞近十四小时的航班,提前了足足两个小时落地在芝加哥奥黑尔机场。“很抱歉我们提前了太多,机场还在努力安排登机口给我们,感谢您的耐心等候。”在乘务长的不知道第几遍通知后,我终于按时站在了提取行李的传送带边。
像往常一样,我站在传送带的远端——就是那个椭圆形带状物体的边缘,离箱子们一个个钻出来的那个洞口最远的位置。这个位置往往人最少,因此不用和别人挤着去抢飞奔着寻找自由的我的箱子,或者担心搬箱子时蹭到别人而凭生的几句道歉和寒暄。与我相反地,大多人都会站到洞口附近的位置,就好像生怕取晚了箱子就会不翼而飞一样。怎么会呢?传送带循环往复,只要别人不错拿走你的箱子,它总会在那里一圈一圈兜着的。不急。今天也是一样,或者说今天我的预判尤其准确——除我之外,没有一个人站在传送带的这一端。所有人都乌压压地挤在洞口那儿神色不安地等着,偶有几句听不太清楚的低语。我没有太去注意别人(当然也不希望别人来注意我),所以也无言地等在这一端。为了避免尴尬,我戴上了脖子上挂着还没收起来的耳机,伴着心跳假装有音乐地开始摇晃起自己的头来。
箱子一直没来。我在那里摇了快十分钟头,看着一个红得刺眼的箱子在我面前周而复始地转了四五圈,也没有看到自己的箱子。那一头的人渐渐少了下去,很多人搬走了他们的箱子,推着堆满箱子的行李车笑语晏晏地走了。这难道不诡异吗?刚刚还紧张得要死的人转眼喜笑颜开,只是为了一个明知道不可能丢的箱子?太荒谬了。但我没心思去吐槽他们,我的心思全在我那迟迟不来的箱子上。我把耳机摘了下来挂在脖子上,过了不多久又戴了回去,然后又摘下来。我看着手机上的时间从四点变成五点,又一分钟一分钟地爬向六点。我感觉有点冷,可能是因为上海和芝加哥的温差,但大概还是因为饿了。下一个航班的信息占据了原本属于我的屏幕,是来自哈瓦那的航班。芝加哥还有去哈瓦那的航班吗?哈瓦那在哪个国家来着?我脑子里出现了热带雨林,颜色艳丽的鸟,五彩斑斓的紧挨着彼此的小房子和看不到边的雪白的沙漠。沙漠中央,离我无限远的地方,立着一个行李箱。它那样远,感觉就算我是那只鸟,尽全力飞去,也要一天一夜、不眠不休才能飞到。可如果我是只鸟,我要怎么把它取回来呢?用喙叼回来吗,还是说用爪子?怎么都不可能吧,箱子对我来说也太重了。想着,我把手往前伸,一伸,就够到了箱子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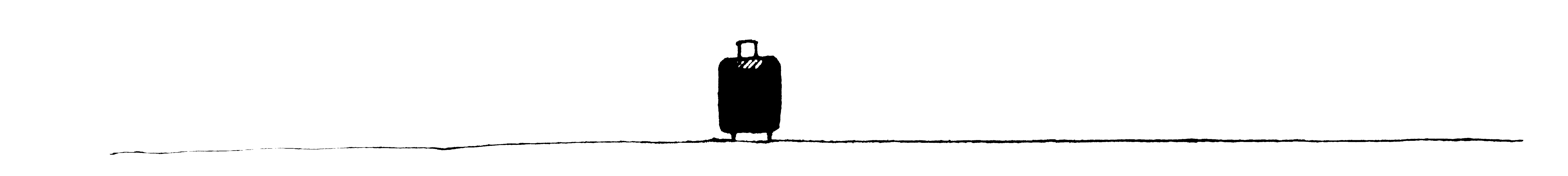
它果然很沉,我两只手用力才把它搬了起来。这是一个黑色的软箱。虽然是布料,但很结实,遍布于表面的破损也说明了这种面料的经久耐用。得有些年头了吧,这箱子?我很好奇是谁拥有这个奇异的箱子,以及一切关于这箱子的故事。它的主人肯定带着它走过很多很多国家,去海拔最低的地方见过最遥远的银河,去离天空最近的地方弹着吉他等过日出,去雪山,去海边,去草原,去河湾,去开满花的谷地。这么一想,这个箱子甚至比我幸福了。这不再是个奇异的箱子了,这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箱子。我屏住呼吸,凑近了看。箱子上没有一个字,也没有任何显示它属于过任何人的标志。它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呢?难道不是只要出现在这里的箱子就必然是空运过来的,因而也必然贴了行李的标签吗?要是那个马虎的工作人员被发现了,一定会被开除吧。他或许已经被开了,因为一定还有别人的箱子被忘贴了标签——不对,他或许永远不会被开除,因为这个箱子已经到了这里,到了我手里。说明没有别人看到过它,更不会有人注意到它没有被贴标签——而我,我不会去举报那人的,我甚至不认识那人,这箱子也不是我的。不对,它是我的吗?我一个哆嗦,被自己这个诡谲的念头吓了一跳。这怎么可能是我的呢?我一共也只有过三个行李箱。最近买的那两个,是黑色的硬质箱子,合成塑料的弹性很好,给人一种永远不会坏的感觉。再早一点用的,是一个有竖直凹凸条纹的黑色铝箱。还记得我刚买到那个箱子的时候心情特别好,是一种小孩子期待了一年终于收到心仪的礼物的那种好。可惜铝箱金玉其外,太容易刮花,更容易有凹陷,几趟国际航班下来就面目全非了。再早几年,我依稀有印象用的是一个黑色的布箱。时间久远,牌子早已经忘记了,甚至连好不好用也不太记得。我对它最后的回忆停留在若干年前的某一趟航班。那时,因为落地后我的箱子迟迟不来,我就去服务中心问。结果它就在那里,一条拉链拉开一半,另一条不翼而飞。工作人员说因为箱子托运途中破损了,所以也刚好在找我。在漫山遍野的道歉声中我签了委托书,请他们找维修商把那箱子修好了寄给我。我写下了我当时的地址,马马虎虎地签了字,就离开了。之后我就不记得了。那个箱子有曾寄回来过吗?完全想不起来。我是搬家了吗?从哪里搬去哪里,我也毫无头绪。真的太久了,就像发生在上辈子一样,只记得故事的碎片,但怎么也连不成一整条线索来。我想不起那天之后又发生了什么,也想不起被我遗忘的那个箱子的模样。我低头看着眼前这个陌生的、古老的、破损的、奇异而又幸福的箱子,把自己的生日输进了密码锁。箱子开了。
可我却不敢打开了。
